购物指南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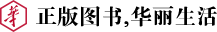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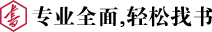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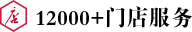
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7572号 丨 京ICP证 京B2-20171652号 丨 京ICP备16042375号-2
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新出发 京批字第直200352号 丨 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书编号:(京)-非经营性-2022-0045
Copyright © 2015 - 2024 新华互联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权所有
客服热线:4006666505
注册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135号39号楼1层101、2层201